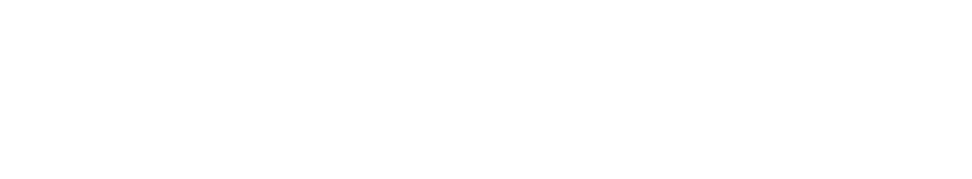相信很多人都有過一個“尋寶”夢——在藍色的海洋世界里,偶然發現一個裝著寶藏的沉船。歷史上出現過不少偶然發現沉船的故事,關于沉船的“奇聞軼事”,也多次出現在各種形式的文藝創作中。
沉船中不僅可能有著奇珍異寶,也留存了文化的印記,是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等研究的重要對象。然而,要找到一艘沉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沉船信息記錄不明確、水下能見度極低、生態侵蝕與掩埋、洋流影響……這些因素疊加起來,使得在覆蓋地球71%面積的海洋中找到沉船,迄今仍是世界級的難題。
而今年3月,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東海研究站(以下簡稱東海研究站)的聲學考古團隊,利用聲學探測與潛水考古相結合的方式,在斯里蘭卡的海域中搜尋到了一艘此前未探明的海底沉船。

實驗用船
經初步推測,這是一艘百年前的大型西方貨輪,相關的鑒定和發掘工作正在加緊推進中。但這件事的源頭,卻和中國歷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鄭和有關。
沉船
1405年,鄭和帶著浩浩蕩蕩的船隊開始了首次遠航。此后28年,船隊七下西洋,鑄就了一段傳播中國文明和技術的佳話。
然而,隨著資料損壞、歲月變遷,這只船隊逐漸在歷史中隱沒。人們只能從史書的只言片語中、旅途各國口口相傳的故事中,尋找一些蛛絲馬跡。歷史記錄中四十四丈四尺長、一個足球場般大的“寶船”也再未出現過。
寶船到底長啥樣?明朝的造船技術真的這么高超嗎?兩萬余人如何在漫長的旅途中生活?人們對這些問題充滿好奇,卻苦于找不到船一探究竟。
2005年,在鄭和初下西洋600周年之際,東海研究站的核心骨干科研人員、如今的中斯海上聯合探測首席科學家胡長青開始思考,是否可以通過聲學的手段進行探測,尋找鄭和沉船的蛛絲馬跡。
“盡管歷史資料中沒有明確記載,但從當時的航海水平、沿途發生過戰爭等判斷,不可避免會有沉船。”胡長青告訴《中國科學報》。
在海平面幾十米下的海水中,光的傳播效果極差,即便帶著光源,能見度也不超過10米。聲波則可以輕松到達幾百米甚至更遠處,回聲的時間差和強度差,更是攜帶著終點處的環境信息。基于此原理,科學家們開發了圖像聲吶技術,用于“看見”海洋深處。
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以下簡稱聲學所)正是我國聲學領域的代表性科研機構,先后開發了多個自主知識產權的水下探測設備,如多波束測深儀、側掃聲吶、合成孔徑聲吶、淺地層剖面儀等。這些技術廣泛服務于國民經濟主戰場的同時,也為探測海底沉船提供了新的工具。
窗口
“20年前,水下考古水平整體仍較薄弱,可用的探測設備也很少。東海研究站正好有一些能用于探測掩埋目標的設備,我們就思考將其用于探測鄭和團隊的沉船。”胡長青回憶道。
在聲學所牽頭下,我國科研人員仔細看了幾遍鄭和船隊歷次下西洋的路線圖,把第一站鎖定在阿曼海域。2007年,“鄭和沉船遺骸探查”中阿國際合作項目正式開啟;2009年,聲學所科研團隊根據考古學家劃定的可疑區域,利用側掃聲吶設備圈定了12個沉船疑似點;2012年,團隊進一步利用合成孔徑聲吶系統確定了6個沉船目標。
這次成功合作的經歷,給了胡長青等科學家很大的信心,但要找尋鄭和船隊的沉船,海域面積還是不夠。
2013年,我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鄭和下西洋的路線,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倡議得到了斯里蘭卡的積極響應。斯里蘭卡位于印度半島南端,自6世紀以來便是印度洋海上貿易的貨物集散地,也是鄭和下西洋的重要中轉點。
中國科學院迅速抓住了這個時間“窗口”,積極籌備與斯里蘭卡關于“在斯里蘭卡海域探測鄭和沉船”的合作,并于2014年9月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
2015年,鄭和下西洋610周年之際,第一次科考工作正式啟動。
當胡長青帶領聲學考古團隊來到斯里蘭卡準備大干一場時,卻被潑了一盆冷水。由于斯里蘭卡政府更迭,上屆政府沒有及時簽發出海試驗許可證,團隊無法出海開展試驗。
他們第一時間重新申請相關批件,但遲遲沒有消息。成員們很是著急,加上水土不服,好幾個都病倒了。
團隊核心成員、東海研究站研究員趙梅主動站了出來,前往科倫坡同各方交涉。經歷烈日下幾小時的等待、往返于不同部門、多方斡旋溝通后,趙梅終于拿到了這張寶貴的出海許可證,也“治”好了同事們的病癥。
“心里只有一個念頭,不能坐以待斃,有一點希望就要去闖一闖。”趙梅回憶道。
聲學考古團隊十分珍惜這個機會,帶著各種聲學設備開始探測,并在斯里蘭卡西南部貝魯維勒港外海的海底發現了一處疑似海底沉船。
2016年、2017年,團隊連續兩年前往斯里蘭卡,分別使用高分辨圖像聲吶和水下機器人(ROV),對該疑似目標進行探測和核實,確認其為一艘未探明的海底沉船。

操控水下機器人
胡長青解釋:“船身上往往布滿了珊瑚等海洋生物,因此需要仔細觀察。我們一般先把可疑的目標圈出來,再反復回看,必要時還會到相關區域回溯。”
由于該沉船在海面下65米處,超過了常規潛水的深度,聲學考古團隊與斯里蘭卡方商定,下一步對該海底沉船進行潛水探測。
但變故突生,種種原因干擾下,后續海上考察活動一再擱置。“斯里蘭卡的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我們的科考活動不可避免會受到國際局勢影響,因此抓住時間窗口十分重要。”胡長青說道,“因此,我們一直在積極推進合作,停滯期間,雙方也在探討下一步探測方案、開展鄭和相關的學術交流活動。”
八年后,“窗口”終于再次出現,第四次科考立即被提上日程。
過程
胡長青笑道:“我們現在要往后退了,得讓年輕人沖在前面。”
八年間,趙梅接下了胡長青的班,成為聲學考古團隊新的負責人,一些年輕人也逐漸成長起來。
今年參與深潛探測成員中,就有3位“90后”小伙——孫東飛、郭政、羅宇涵,他們分別負責測線導航和站位確認、ROV水下攝像,探測設備布放和數據處理以及側掃聲吶對海底沉船的探測。
盡管已經對沉船位置有了九成把握,但剩下的一成仍然不容易。
“不像地面上用GPS定位,能夠精確到某一個點。”胡長青介紹,在到達預定海域后,需要布放側掃聲吶對沉船進行定位。側掃聲吶并非直接固定在船上,而是通過電纜和船連接,兩者之間會有一定的距離和角度,必須精確設計科考船的航行路線和方向。

團隊成員正在吊放側掃聲吶拖魚
為了確保“實操”時的效率,團隊在出發前往斯里蘭卡前進行了充分的準備。一方面,中斯雙方在線上進行充分溝通,探討海上試驗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并列出解決方案。另一方面,幾個年輕人反復調試確認各種設備的參數和性能,并提前在水環境中測試。
試驗當天,他們按照規劃好的十字交叉側掃航路,先從北向南進行掃測,然后又從東向西進行掃測,獲得了不同方位的沉船聲圖,從而確定了沉船的位置。
隨后,由斯方的潛水員帶著成像設備,到達沉船位置上方后潛水作業。考慮到深潛裝備呼吸氣體的特殊性,每天只能開展一次深潛,海底作業時間為20分鐘,加上下潛和上浮,單次作業需要兩小時。
這兩小時,科考船上等待著的成員們頗為緊張。潛水員浮出水面后,他們第一時間圍上去,看“新鮮出爐”的沉船視頻。
“就像是努力學習后考上了心儀的大學,覺得這一切都值了。”東海研究站工程師郭政形容。
在聲吶圖像上,可以清楚看到沉船的全貌。這艘鋼結構船長約120米,寬度約20米,船艏方向的船體坐在海底,錨機、錨鏈、船首右側的錨清晰可見,左側的錨則消失了。船的后半部分左側船舷往外凸出破損,船尾往左側傾倒,船艏方向朝南。

使用側掃聲吶探測到的海底情況,圖中左側物體為沉船
“這說明船的左后部受損嚴重,是從科倫坡港裝載貨物后駛離時發生了意外。”郭政介紹,“根據船體結構和造船技術,以及沉船表面珊瑚生長狀況,我們推斷這是百年前的大型西方貨輪。”
未來
“有點遺憾,這并不是鄭和船隊的沉船。”胡長青坦言。
但這段“尋船”經歷,依然有其考古和文化意義。在鄭和下西洋620周年之際,聲學考古團隊憑著多年堅持,證明了聲學技術在海洋考古中的重要作用,也為我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科技與文化合作建立了可借鑒的模式。
如今,中斯雙方正在規劃下一階段的合作。“斯方希望能夠建立兩國聯合研究中心,在后續的水下考古、文物鑒定和保護等方面開展更深度的合作。”胡長青表示,“我們聲學考古團隊也正在計劃開展另一處海域的探測工作。”

聲學考古團隊與斯方人員合影
東海研究站也在繼續加強自身的基本功。
“過去十多年間,我國在水下聲學探測設備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應用也從原有的海底地形地貌探測擴展到沉船考古、海洋生物研究等領域。”東海研究站站長許偉杰表示,“在此過程中,東海研究站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但要想在地球上如此廣闊的海洋世界中“挖寶”,設備依然有著很大的進步空間。
盡管聲波在水下可以傳播較遠距離,但是成像卻并不簡單。往往需要先航行到沉船位置附近,才能得到較準確的探測結果。
隨著智能化、無人化設備的發展,未來有望讓探測設備在海底、復雜環境下自主探測,釋放人力的同時,覆蓋以往難以到達的區域。
“我們希望擴大設備單次掃測的覆蓋范圍,同時提高設備成像精度,不僅看清沉船外觀,也能初步探明內部結構。”許偉杰說道,“我們也將繼續發揮東海研究站的優勢,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為我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科技發展貢獻力量。”
作者:《中國科學報》 記者 江慶齡?王韞綺
來源:《中國科學報》?(2025-8-7?第3版 綜合)
報道鏈接:https://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t=&id=41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