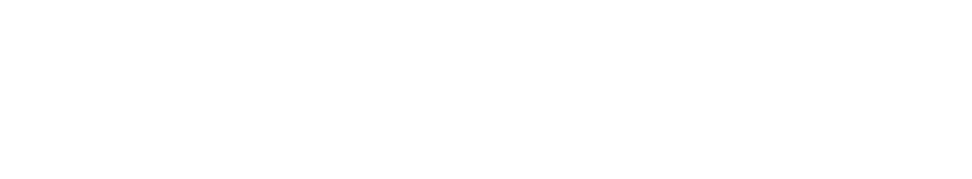馬大猷(1915-2012),廣東汕頭人。1936 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1940年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聲學家、物理學家和教育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中國現代聲學的重要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

開創哈佛大學先例的中國留學生
在少年時代目睹祖國的積貧積弱后,馬大猷便立下“科學救國”的信念。1936年,馬大猷獲得北京大學理學學士學位,同年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后來,馬大猷僅用兩年時間,就獲得了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39年) 和哲學博士學位(1940年),這在哈佛大學是沒有先例的。求學期間,馬大猷嶄露頭角,他被認為貢獻了世界聲學史上“波動聲學的一個基本公式”,取得了令美國聲學界矚目的成就,這確立了他在現代聲學研究中的地位。馬大猷雖身在國外,仍心系祖國,不忘抗日,多次參加愛國華僑組織的“一碗飯運動”,為抗戰和救濟難民捐款。
博士畢業后,馬大猷面對祖國山河破碎,工業基礎薄弱,科研水平單薄,迫切需要人才的現狀,立刻踏上歸途,返回燃遍抗日烽火的祖國,選擇任教于西南聯合大學,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在這樣艱難困苦的歲月里,馬大猷生活簡樸,住在“望蒼樓”前院大約10平米的小屋里,屋內的陳設只有床、書桌、書架和盥洗用具。
馬大猷為人正直,愛憎分明,面對國民黨特務的襲擊,他挺身而出,聲稱自己是西南聯合大學工學院的負責人,嚴厲斥責對方并要求立即離去。馬大猷保護教學環境和師生安全的正義行為,受到學生們的愛戴和敬佩,也為學生們樹立了榜樣。

馬大猷(右三)在西南聯合大學
敢于對“大家”的理論說“不”
馬大猷對待學術研究總是認真仔細,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他圍繞國家發展“兩彈一星”的戰略目標,先后開展了核爆炸偵察和聲學探測、大氣層核爆炸的次聲監測等一系列重要研究工作,為開拓中國現代聲學事業打下堅實基礎。
馬大猷即便在繁忙的科研事務管理中,也不忘保持對科學研究的嚴謹態度和求實精神。莫爾斯是20世紀上半葉最偉大的理論聲學家之一,馬大猷的導師亨特就是在莫爾斯的理論影響下,開始與學生們(馬大猷和有“美國聲學權威”之稱的白瑞內克)作矩形室內的聲衰變分析的。1989年,馬大猷就指出莫爾斯的室內聲場經典簡正波解中,應當加入代表直達聲的一項,使其物理意義更加明確。對這個問題,馬大猷似青年科學家一樣尖銳直率,他批評莫爾斯的室內受迫振動理論“只有數學,缺少物理”。他認為,莫爾斯沒有認真分析聲源的作用,就貿然投入數學處理。實際上,他的批評不完全是針對莫爾斯,也是提醒更多只注意改進模型算法而忽略物理分析的青年學者。
不說客套話,只說心里話
1962年2月,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馬大猷出于對國家大事的關心,在物理組的小組會上率先大膽發言,促成對知識分子的“脫帽加冕”。馬大猷說出了大家的心里話,眾人稱贊馬大猷的這一舉動為“一馬當先”。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還在中國科學院的會議上表揚馬大猷,說他不說客套話,只說心里話。陳毅副總理在3月5日和6日,分別向會議代表宣布,要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也就是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
馬大猷是一位治學嚴謹的科學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一直十分關心科學教育事業,堅持理工結合的教育思想,注意培養青年學者的理論素養和動手能力。“有時看到一些科學家為引進日本產品還是德國產品而爭論,我臉都紅了。”這是馬大猷的話語。他強調科學研究的原創性,他曾經說過:“自然科學研究中,以創造性勞動取得的發明才是評價標準,科學只承認第一,不承認第二。”
即便在耄耋之年,馬大猷也積極建言獻策。他上書國家,呼吁要加強基礎研究工作,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斷提高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不斷努力。